
 2022-07-06 14:51:20
2022-07-06 14:51:20
 凤凰大语文
凤凰大语文

《景阳冈》怎么上?
文 | 祁智
《景阳冈》这个课文题目,我是很欣赏的。尽管以“武松打虎”为题也贴切,但我还是更愿意倾向“景阳冈”。
景阳冈是地名。以地名为题目,有氛围,让人全身一紧,仿佛“那一阵风过”;很含蓄,“武松打虎”,还是直白了一些,一览无遗;有韵味,冈上冈下,何止一人一虎?酒旗迎风,夕阳西下,草木有声。
章回小说是传统文化的一种。将小说改变成戏剧,以地名为剧名,屡见不鲜,比如《长坂坡》《武家坡》《淮河营》《十字坡》《野猪林》。即使现代京剧《芦荡火种》,也最终定名《沙家浜》。将章回小说节选成文,取名不可随意,应该尽量贴近传统,让文气一脉相承。
最关键的是,以“景阳冈”为题,不影响“武松打虎”。
回到《景阳冈》怎么上。
先设想一下。假如课文直接从“那一阵风过处”开始,是否成立?我以为,除了个别词句作必要调整之外,没有问题。武松打虎,有打的过程、方式、结果,是完整的一件事。
既然这样,为什么在这之前,要用大段的文字,说武松喝酒、上冈呢?
还是设想一下。武松如果没有喝酒,不是自己上冈,你直接把他空投到景阳冈上,他会打虎吗?他会打你。
即使是好汉武松,打虎也是非正常行为。要让非正常成为正常,需要有十足的理由。说白了,就是要让武松这个根本不想打虎的人,一步一步“上”冈。
酒家是施耐庵安排的。
酒家不知道武松不知道有虎——天底下的人都知道,这位客官怎么可能不知道呢?他一定这么想。所以,他按常规,一碗一碗一碗,给武松筛酒。
“三碗不过冈”,并不是喝了三碗才不过冈。“三碗”是上限,身子弱一点,半碗都上不去,不要说“过”了。
武松到了“上”限,但这不是他的“上”限。他是武松,所以,又“上”三碗,还“上”三碗,再“上”三碗,最后“上”六碗,计“上”十八碗老酒,加“上”四斤熟牛肉。
这么大的酒量、饭量,是说武松并非常人,是要让他“上”去。假如他酒量饭量“上”不去,“上”去了也打不了。
酒名“出门倒”,是施耐庵取的,为武松当堂不倒找到理由——倒了就“上”不去了。但十八碗过后,“出门”也不“倒”,直到“上”去了才有反应,更是说武松非一般的好汉,也为他打虎找到胆子——他如果神志清醒,必定一溜烟下去了。
“告示”也是施耐庵安排的。
酒家喊走出酒店的武松回头看“官司榜文”,武松本来就烦他多嘴,怎么可能信他,所以不过脑子,说“便真个有虎,老爷也不怕”。假如他知道冈上真有虎,估计他宁可喊酒家老爷,也断然不会“上”。
半路上,武松看见树皮上刻“两行字”。他非但不信——衙门的公文怎么可能刻在树皮上,而且很自信地“洞穿”了酒家的“诡诈”。
当“印信榜文”映入醉眼,武松第一反应是退,跟着反应是退回去怕被耻笑,“存想了一回”,“上”来的酒劲让面子下不去,“怕甚么!且只顾上去,看怎地!”
武松在这里的犹豫与侥幸,是说武松是条好汉,但好汉也是人。
武松就这样,被施耐庵撺掇上冈。他面对的,已经是两个“冈”,一个是三碗不能过的,一个是六个时辰和单身不许过的,难度翻了一番。而且,因为酒劲发作,他跑不掉。
没有前面这些絮絮叨叨,武松怎么可能在冈上?

现在要说虎。
“吊睛白额”大虫受施耐庵派遣,来到景阳冈上。现在,它“又饥又渴”。
“又饥又渴”是老虎持续了好几天的状态。这很重要。在“坏了二三十条大汉性命”之后,大家没有绝对把握,坚决不过冈,搞得老虎多日没进食,“又饥又渴”,不得不把晚上捕食的习惯,改变为不分昼夜。这既印证了酒家的规劝,也给武松增大了危险。“又饥又渴”的老虎,终于见到食物,被彻底激励,憋足劲一扑、一掀、一翦。
设想一下。如果老虎不是一连几天“又饥又渴”,三招过后,虎劲虽然要泄一半,但不至于那样不堪。
老虎如强弩之末,武松的酒肉正好转化成能量。在“惊”“闪”“躲”“闪”“慌”之后,伟大的打虎,正式开始。
武松打虎,关键在“打”。
“打”不好看,怎么“打”才好看。所以,武松在虎身上找到一连串的“动词”。
相传,施耐庵为了写好这一段,骑在板凳上边打边找感觉。他并不知道虎能不能被打死、什么时候被打死,所以不停地打。“手脚都疏软了”,才不得已停下来。他打出了身临其境的感觉,不禁帮武松后怕,生怕“又跳出一只大虫来”,慌忙安排武松趁着刚黑的天色,“一步步挨下冈子来”。
不可能发生的事,发生了,是因为“铺垫”;很难写好的事,写好了,是因为“真实”。酒店里,事情靠对话交代,清楚而风趣;酒店外,情节靠动词推进,扎实而紧凑。店里店外,冈下冈上,打前打后,浑然一体。
很可能有人会说,这样“上”、“上”这些,学生能懂吗?我以为,课文如此,不讲不行。上课,就是要把这些讲出来,讲透彻。讲了,如果学生听不懂,一定是老师没讲好,没讲对。
而且,老师如果不讲这些,想讲什么?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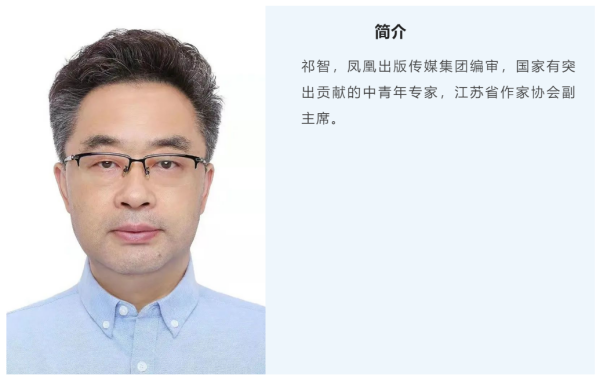





 网站首页
网站首页 关工动态
关工动态 “大思政”教育
“大思政”教育 心理健康
心理健康



